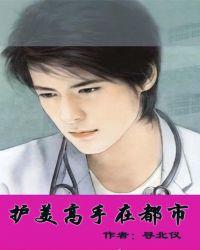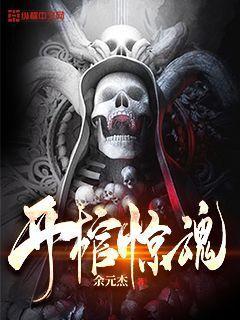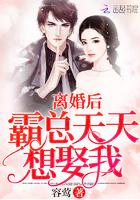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32章(第1页)
1946年回国,我到北大来工作。
我兴趣最大、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,由于缺少起码的资料,已无法进行。
我当时有一句口号,叫做:&ldo;有多大碗,吃多少饭。
&rdo;意思是说,国内有什么资料,我就做什么研究工作。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
不管我多么不甘心,也只能这样了。
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。
解放初期,我翻译了德国女小说家安娜&iddot;西格斯的短篇小说。
西格斯的小说,我非常喜欢。
她以女性特有的异常细致的笔触,描绘反法西斯的斗争,实在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。
以后我又翻译了迦梨陀娑的《沙恭达罗》和《优哩婆湿》,翻译了《五卷书》和一些零零碎碎的《佛本生故事》等。
直至此时,我还并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。
我用力最勤的还是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。
我努力看书,积累资料。
50年代,我曾想写一部《唐代中印关系史》,提纲都已写成,可惜因循未果。
十年浩劫中,资料被抄,丢了一些,还留下了一些,我已兴趣索然了。
在浩劫之后,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,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。
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,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,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翻译工作,从来也没想到出版问题。
我选择的结果就是印度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。
大概从1973年开始,在看门房、守电话之余,着手翻译。
我一定要译文押韵。
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,我就坐在门房里,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,大半都不认识,只见眼前人影历乱,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。
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,路上我仍搜索枯肠,寻求韵脚,以此自乐,实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上面我谈了六十年来我和外国文学打交道的经过。
原来不知从何处谈起,可是一谈,竟然也谈出了不少的东西。
记得什么人说过,只要塞给你一支笔,几张纸,出上一个题目,你必然能写出东西来。
我现在竟成了佐证。
可是要说写得好,那可就不见得了。
-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
-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
- 影帝从高考开始苏明华雅玩居士
- 开局一个明末位面桃符
-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
-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
- 七位神明月地上霜
-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
- 相声贵公子胖子爱吃炖豆角
-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
- 我真的不想当学霸疯子C
-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
- 大明:我,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
- 雨落影视诸天明少江南
- 支教五年,大明成了日不落帝国落寞的花生
- 这个导演来自西虹市小新吹泡泡
- 北阴大圣蒙面怪客
- 黑石密码三脚架
- 海贼中的最废果实烈焰枪骑兵
-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
- 从超神学院开始的氪星人天道经
- 死神之千年血战王刃西索
- 我的青春我的爱林梓杨
-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
-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
- 仙秦:开局大雪龙骑,我举国伐天江山烟雨
- 毕竟我是你妹,你是我哥别狗咬了
- 爱一场沉华燕
- 修魔有道即墨若谷
- 天命:从大业十二年开始赵子曰
- 剑里乾坤浅墨清语
- 真没开!我的植物和僵尸太强了!夜风侠
- 抗战:从八佰开始痴冬书亦
- 纠缠十年,我死后前夫才放手小甜豆丁
- 生而不凡林北苏婉
- 星际领主:召个魅魔当秘书官七斤流年
- 足球生涯:从躺冠到成为传奇少糖少冰加枸杞
- 普罗之主沙拉古斯
- 战争领主:万族之王楚逸
- 怎么就成万人迷了[快穿]丧团子
- 都成典狱长了,告诉我是卧底?睡到十点醒
- 山村乡野神医纸上情书
- 八零日常:小辣椒一人干翻全村!金满满
- 网游之无极限陈玉皓
- 乾坤龙灵十月洋
- 从武侠开始飞升西游世界最爱吃牛肉
- 我的替身是史蒂夫栖月幽蓝
- LOL:这个男人太听劝了!青石子
- 我在明末修仙瑾珺
- 军婚火辣辣:白莲花她讹上黑阎王三里纯
- 团宠锦鲤妻:我带着盲盒系统无敌了星河逐风
- 小龙崽的豪门后爸菁芸
- 致遥远的你欧娜
- 他藏匿的时光飞夜
- 变成少爷的漂亮小可爱后,他摊牌了赤色轨
- 今日宜沉沦沉官
- 离婚后,热恋中!于他在婚综秘吻掌心有颗糖
- 没想到我竟被龙拆吃入腹紫玖岛
- 康熙老认为我是仙女转世(清穿)欧山之南
- [重生] 清冷美人O长官竟是天然撩若水
- 夭寿!反派嫁我为妻了香菇脆肉丸
- [综漫] 爱穿越的森缘一莲蝉
- 卑微小可怜重生后成了撒娇精[ABO]温茶
- 漂亮反派被龙傲天盯上了懒得一批
- 紧跟时事(人蟒 h 哀牢山)她与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