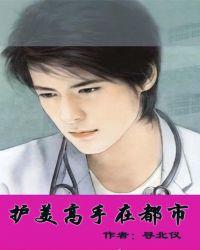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31章(第3页)
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、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。
魏尔兰主张:首先是音乐,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。
这符合我的口味。
但是我反对现在的所谓&ldo;朦胧诗&rdo;。
我总怀疑这是&ldo;英雄欺人&rdo;,以艰深文浅陋。
文学艺术都必须要人了解,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(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就了解),那何必要文学艺术呢?此外,我还喜欢英国的所谓&ldo;形而上学诗&rdo;。
在中国,我喜欢的是六朝骈文,唐代的李义山、李贺,宋代的姜白石、吴文英,都是唯美的,讲求辞藻华丽的。
这个嗜好至今仍在。
在这四年期间,我同吴雨僧(宓)先生接触比较多。
他主编天津《大公报》的一个副刊,我有时候写点书评之类的文章给他发表。
我曾到燕京大学夜访郑振铎先生,同叶公超先生也有接触,他教我们英文,喜欢英国散文,正投我所好。
我写散文,也翻译散文。
曾有一篇《年》发表在与叶有关的《学文》上,受到他的鼓励,也碰过他的钉子。
我常常同几个同班访问雨僧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,有名的水木清华之匾就挂在工字厅后面。
我也曾在月夜绕过工字厅走到学校西部的荷塘小径上散步,亲自领略朱自清先生《荷塘月色》描绘的那种如梦如幻的仙境。
我在清华时就已开始对梵文发生兴趣,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我的兴趣。
但由于当时没有人教梵文,所以空有这个愿望而不能实现。
1935年深秋,我到了德国哥廷根,才开始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,后又从西克教授学习吠陀和吐火罗文。
梵文文学作品只在授课时作为语言教材来学习。
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,西克以耄耋之年出来代他授课。
这位年老的老师亲切和蔼,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学问和盘托出来,交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。
他先后教了我吠陀、《大疏》、吐火罗语。
在文学方面,他教了我比较困难的檀丁的《十王子传》。
这一部用艺术诗写成的小说实在非常古怪,开头一个复合词长达三行,把一个需要一章来描写的场面细致地描绘出来了。
我回国以后之所以翻译《十王子传》,基因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当时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,没有余暇来搞梵文文学,好像是也没有兴趣。
在德国十年,没有翻译过一篇梵文文学著作,也没有写过一篇论梵文文学的文章。
现在回想起来,也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学。
我的兴趣完完全全转移到语言方面,转移到吐火罗文方面去了。
-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
-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
- 影帝从高考开始苏明华雅玩居士
- 开局一个明末位面桃符
-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
-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
- 七位神明月地上霜
-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
- 相声贵公子胖子爱吃炖豆角
-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
- 我真的不想当学霸疯子C
-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
- 大明:我,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
- 雨落影视诸天明少江南
- 支教五年,大明成了日不落帝国落寞的花生
- 这个导演来自西虹市小新吹泡泡
- 北阴大圣蒙面怪客
- 黑石密码三脚架
- 海贼中的最废果实烈焰枪骑兵
-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
- 从超神学院开始的氪星人天道经
- 死神之千年血战王刃西索
- 我的青春我的爱林梓杨
-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
-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
- 您完全不按套路施法是吗星声
- 玫瑰不太乖沉官
- 真相漩涡-推理篇雨润静
- 苟成圣人,仙官召我养马任我笑
- 凌云行之起于微末甘鹊
- 重生就退婚,白莲花前妻跳脚了你滴答案
- 混沌神针木子末末A66
- 策马大明纸花船
- 超级修真弃少木木鱼猫
- 绝世村妇小白楼
- 病态吻!错撩反派后被亲懵强制宠君折柳
- 我团宠小师妹,嚣张点怎么了瑰夏
- 鬼岛.堕天使的华丽诅咒紫园老师
- 穿成豪门弃女,她靠玄学封神息间雨
- 给员工画饼就能暴富芝士丸子汤
- 长生:我在大明被徐达捡回家两广总督
- 心有灵犀:人狗情未了洛清瞳
- 伊底帕斯的诅咒说书人Yang
- 穿越女尊:我用鉴宝赚大钱玉锦
- 快穿之BOSS的小公主不好当柒岁
- 出阳神罗樵森
- 正当关係周敏赫
- 旧日音乐家胆小橙
- 我开的是殡仪馆真不会教斩妖大块牛肉面
- 雄主天下许杰马梦兰我爱富婆
- 地灵灵米子
- 老虎的低音黑白沙漠狐
- 团宠锦鲤妻:我带着盲盒系统无敌了星河逐风
- 穿成恶毒女配后,公主她摆烂了岑十年
- [综漫] 黑狐狸饲养指南冷萃树莓
- 雍正试婚宫女[清穿]玖渔
- 【特传同人】消失的传说筱芷
- 全球异变我靠呼吸躺赢酸辣薄荷
- [柯南同人] 名柯五人组重生后在酒厂相遇白灼夏天
- 在他告白之后(1v1/H)茶里士多糖
- 腰软娇娇一招手,裴爷跪下求亲亲溪禾
- [火影同人] 我在忍界当昆虫学家Connor
- 15级分x学校没教的恋爱不折花
- 一觉睡醒多了个鬼王老公香炒牛河
- 将你从恶梦中唤醒御乔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