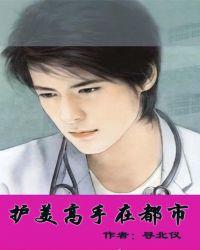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37章(第2页)
说来人们也许不信,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,可十四五年内,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。
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。
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,远或近,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。
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去深圳的。
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。
改毕,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‐‐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。
到时已是下午,在市内转了转,第二天去了沙头角,天黑才回到深圳。
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。
所以在我的印象中,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,只不过途经了深圳。
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,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。
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。
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,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,能勾起我买的冲动。
甚至竟有点儿后悔。
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,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,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。
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。
第一场是《黄天霸》,第二场还是《黄天霸》,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(当时我仍在北影)。
在深圳的短短的时间里,我抽空儿拜访了一位从哈尔滨调到深圳美术馆的画家。
在哈尔滨,他一家四口住两间阁楼。
而在深圳,他住四室一厅。
住处环境相当优美。
附近有集市,买什么相当方便。
尤其海味和副食、蔬菜,在我看来,丰富极了,价格也并不比北京贵多少。
当然,最令我心向往之的,是友人的居住面积,大约近一百平方米。
对他而言,在哈尔滨是不可企及的,恐怕只能是幻想。
对我而言,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,恐怕也只能是幻想,当时我在北影,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间筒子楼。
我非常坦率地承认,我几次萌发调往深圳的念头,主要是幻想能住上宽敞的房子。
我是一个从小在低矮的泥土房中长大的人。
宽敞的房子对我来说,直至一九八六年,一直是个美丽的梦。
深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新,很现代,也很深刻。
它新得好像没有一条老街陋巷,没有像门牙缺洞一样的胡同,没有南方所谓&ldo;棚户区&rdo;或北京所谓&ldo;危房区&rdo;。
-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
-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
- 影帝从高考开始苏明华雅玩居士
- 开局一个明末位面桃符
-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
-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
- 七位神明月地上霜
-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
- 相声贵公子胖子爱吃炖豆角
-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
- 我真的不想当学霸疯子C
-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
- 大明:我,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
- 雨落影视诸天明少江南
- 支教五年,大明成了日不落帝国落寞的花生
- 这个导演来自西虹市小新吹泡泡
- 北阴大圣蒙面怪客
- 黑石密码三脚架
- 海贼中的最废果实烈焰枪骑兵
-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
- 从超神学院开始的氪星人天道经
- 死神之千年血战王刃西索
- 我的青春我的爱林梓杨
-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
-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
- 一道三千非舟
- 我非池中物夜泊秦淮
- 我的:聚宝盆里有一个超级空间冬天有火好温暖
- 妖夫在上林夕煜宸奋起的叶子
- 苏卿卿容阙沈烨的小说免费阅读
- 奥特:开局签到等离子火花九月懒兔
- 快穿:拜金的我在年代文精致利己楠楠的修仙梦
- 宇宙无限食堂小呆昭
- 踏准风口成巨富风起云淡
- 异化武道猪怜碧荷
- 从秘密调查开启反腐之路老爬虫
- 穿越成废柴仵作我靠顶头上司崛起言于卿
- 爆兵:我在末世称霸全球爱吃烧鸡公的阿牛哥
- 开局末世囤物资,我有系统我怕啥养了只猫
- 大梦我仙诀破境难重圆
- 春日灿灿说给月亮
- 什么?让我上天找个仙子当媳妇小煤人
- 魔族第一剑:从离开魔寨入世开始魔系书生
- 长安食肆经营日常添蜜一匙
- 逆势者甲丙男
- 全村都知道她是首辅掌上明珠!双鲤鱼
- 在下一个时空努力生活爱梦的树懒
- 末世之黑暗衍纪哈似橘
- 拳寂万古努力的萌萌
- 不要招惹企鹅王善水流渊
- 一觉睡醒多了个鬼王老公香炒牛河
- 地灵灵米子
- 他藏匿的时光飞夜
- 卑微小可怜重生后成了撒娇精[ABO]温茶
- [原神] 系统上线时我已名扬提瓦特姒子衿
- 漂亮反派被龙傲天盯上了懒得一批
- 离婚后,热恋中!于他在婚综秘吻掌心有颗糖
- 满级大厨养狐日常[美食]芝士鱼丸球
- 变成少爷的漂亮小可爱后,他摊牌了赤色轨
- 软萌小omega他为爱做1[虫族]微雨轻酌
- [火影同人] 我在忍界当昆虫学家Connor
- [重生] 清冷美人O长官竟是天然撩若水
- 糟糕,被师尊盯上了陇月花枝
- 小龙崽的豪门后爸菁芸
- 缀凤【女A男O NP 骨科】旧曾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