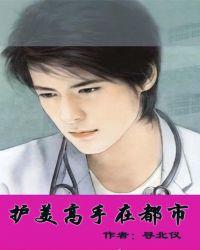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14章(第1页)
我平卧在床上,让柔弱的灯光流在我身上,让寂寞在我四周跳动,静听着远处传来的跫跫的足音,隐隐地,细细弱弱到听不清,听不见了,这声音从哪里传来的呢?是从辽远又辽远的国土里呀!是从寂寞的大沙漠里呀!但是,又像比辽远的国土更辽远;我的小屋是坟墓,这声音是从墓外过路人的脚下踶出来的呀!离这里多远呢?想象不出,也不能想象,望吧!是一片茫茫的白海流布在中间,海里是什么呢?是寂寞。
隔了窗子,外面是死寂的夜,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,不见灯光;不见一切东西的清晰的轮廓,只是黑暗,在黑暗里的迷离的树影,丫杈着,刺着暗灰的天。
在三个月前,这秃光的枯枝上,有过一串串的叶子,在萧瑟的秋风里打战,又罩上一层淡淡的黄雾。
再往前,在五六个月以前吧,同样的这枯枝上织上一丛丛的茂密的绿,在雨里凝成浓翠,在毒阳下闪着金光。
倘若再往前推,在春天里,这枯枝上嵌着一颗颗火星似的红花,远处看,晖耀着,像火焰。
‐‐但是,一转眼,溜到现在,现在怎样了呢?变了,全变了,只剩了秃光的枯枝,刺着天空,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,外面披上这层刚劲的皮,忍受着北风的狂吹,忍受着白雪的凝固,忍受着寂寞的来袭,同我一样。
它也该同我一样切盼着春的来临,切盼着寂寞的退走吧。
春什么时候会来呢?寂寞什么时候会走呢?这漫漫的长长的夜,这漫漫的更长的冬……
《忆往述怀》第一篇:阅尽沧桑《忆往述怀》爽朗的笑声(1)
据说,只有人是会笑的。
我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中,曾经笑过无数次,也曾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。
我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,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,人们天天必须吃饭这样一些极其自然的、明明白白的、尽人皆知的、用不着去探讨的现象一样,无须再动脑筋去关心了。
然而,人是能够失掉笑的。
就连人能够失掉笑这个事实我以前也没有探讨过,不是用不着去探讨,而是没有想到去探讨,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;因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失掉了笑的人,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了笑的人,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,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。
人又怎能失掉笑呢?
我认识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。
虽然他资格老,然而从来不摆老资格,不摆架子。
我一向对老干部怀着说不出的、极其深厚的、出自内心的感情与敬佩。
他们好像是我的一面镜子,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,激励自己前进。
因此,我就很愿意接近他,愿意对他谈谈自己的思想。
当然并不限于这些。
我们有时简直是海阔天空,上下古今,文学艺术,哲学宗教,无所不谈。
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特别是在闲谈时他的笑声更使我永生难忘。
这不是会心的微笑,而是出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。
这笑声悠扬而清脆,温和而热情;它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,一听到它,顿觉满室生春,连一桌一椅都仿佛充满了生气,一花一草都仿佛洋溢出活力。
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,冲出了窗户和门,到处飘流回荡,响彻了整个燕园。
想当初当我听到这笑声的时候,我并没有觉得它怎样难能可贵,怎样不可缺少,就同日光空气一样,抬眼就可以看到,张嘴就可以吸入。
又像春天的和风,秋日的细雨,只要有春天,有秋天,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得到。
中国古诗说:&ldo;司空见惯浑闲事,&rdo;我一下子变成了古时候的司空了。
然而好景不长,天空里突然堆起了乌云,跟着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。
这一场暴风骤雨真是来得迅猛异常。
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,而且也没有听说别人曾经经受过。
我们都仿佛当头挨了一棒,直打得天旋地转,昏头昏脑。
有一个时期,我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,在一个阴森可怕的恐怕要超过&ldo;白公馆&rdo;和&ldo;渣滓洞&rdo;的地方住了一些时候。
以后虽然恢复了自由,然而每个人的脑袋上还都戴着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,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,谨小慎微,瞻前顾后,唯恐言行有什么&ldo;越轨&rdo;之处,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。
我们的处境真比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困难。
- 斗罗之我编造了未来视频符何君
- 东京电子游戏大亨小鸡啄小米
- 影帝从高考开始苏明华雅玩居士
- 开局一个明末位面桃符
- 全职之职业欧皇闪光哈士奇
- 黑龙国度不死长河
- 七位神明月地上霜
- 影帝他不想当太监江公子阿宝
- 相声贵公子胖子爱吃炖豆角
- 我的手机能挖矿卖艺小青年
- 我真的不想当学霸疯子C
- 君临法兰西孤山钓雪
- 大明:我,朱棣第四子星月长江
- 雨落影视诸天明少江南
- 支教五年,大明成了日不落帝国落寞的花生
- 这个导演来自西虹市小新吹泡泡
- 北阴大圣蒙面怪客
- 黑石密码三脚架
- 海贼中的最废果实烈焰枪骑兵
- 诡异星巫白银黑铁
- 从超神学院开始的氪星人天道经
- 死神之千年血战王刃西索
- 我的青春我的爱林梓杨
- 从成为妖怪之主开始咸鱼配饭
- 诸天大明联盟饿祸
- 龙血腾幻羽苍穹
- 超级上门弃婿和他的美女天涯不速之客
- 万象独生颜左关七
- 失恋后,发现好兄弟是清冷校花水生西瓜
- 带女儿摆地摊,全球被我馋哭了!爱吃肉片
- 太荒吞天诀铁马飞桥
- 易孕体质,七零长嫂凶又甜方赢
- 归零:云海梦境,山海有灵雨落时
- 重生地球变成傻子李豆芽
- 离婚后,我被坑上恋综,前妻急了长安名利客
- 一本不正经的修仙感悟一缕喧嚣
- 我在都市筑仙境草本哈根
- 祭祀自己,我成为了神话?神游虚空
- 和法医前男友闪婚后裴若云
- 风流村事人前显贵
- 技能添词条,双职业奶妈井井有条吃榴莲的狐狸
- 爷!认输吧,夫人黑白两道皆马甲一觉三醒
- 综影视:卷王她又开卷了饕老六
- 重生在宝可梦,我的后台超硬热心的冰块
- 快穿之混低保日常喜欢鱼香草
- 财阀独女穿七零卡索娜
- 重生官场:从复仇开始火了买飞机
- 三国:重生赵云,桃园五结义执笔墨画你倾城
- 高武:开局女捕头说我养你是幻是真
- 全民领主:从零开始创造大千世界闪烁星光
- 首席舰长[星际]慕君年
- 病弱美人的反派人设崩了红叶月上
- 变成少爷的漂亮小可爱后,他摊牌了赤色轨
- [柯南同人] 名柯五人组重生后在酒厂相遇白灼夏天
- 穿书成恋爱脑霸总后moontage
- 缀凤【女A男O NP 骨科】旧曾谙
- [综漫] 黑狐狸饲养指南冷萃树莓
- 雍正试婚宫女[清穿]玖渔
- 刁奴欺主无韵诗
- 漂亮反派被龙傲天盯上了懒得一批
- 夭寿!反派嫁我为妻了香菇脆肉丸
- 致遥远的你欧娜
- [排球少年同人] 不会发球的副攻不是一个好自由人森林守望者
- 糟糕,被师尊盯上了陇月花枝
- 地灵灵米子